国之宝桢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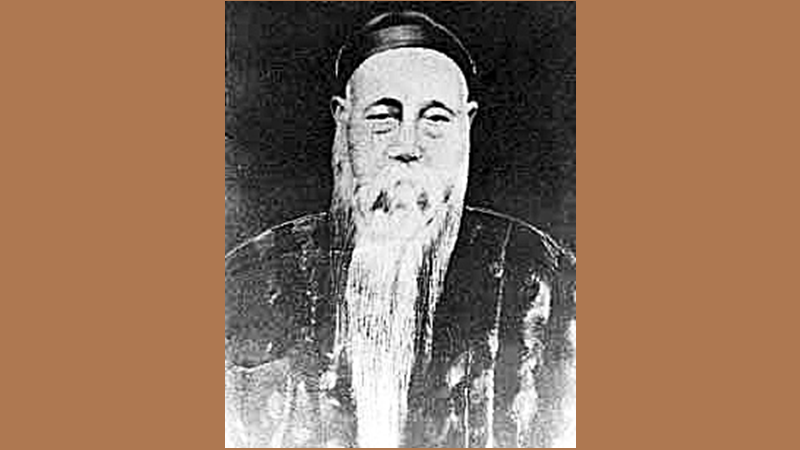
家风长不长,廉字第一防。
咸丰三年(1853年),33岁的丁宝桢考取进士,先后任岳州、长沙知府,48岁任山东巡抚,57岁升任四川总督。“平远奇男抚东督川勇于任事惩恶扬善一身正气,晚清重臣爱国为民睿智超群廉洁奉公两袖清风”,这副对联概括了丁宝桢一生的功绩,也是他德政双馨的人格写照。
丁宝桢并非出身名门望族,但丁氏家族却长盛不衰,传至丁宝桢已历百年。乾隆初年,丁宝桢先祖丁福汉,经商来到贵州平远州牛场镇,见这里山清水秀、民风淳朴,就定居下来。丁福汉虽是生意人,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。丁福汉之子丁公俊深受影响,赋诗以言志:
“人非圣贤无高下,世代忠良不可差。读书耕田不误时,精忠报国品自嘉。廉洁奉公身高洁,尊老爱幼在天涯。一旦蒙恩受命时,不负朝廷不负家!”
诗中阐述了人无高下,品有忠否;平日读书耕田,常思精忠报国;一旦出仕为官,必须不负家国。其核心在于一个廉字,立身高洁看廉品,走遍天涯爱当先。
正是这首被丁氏后人看作家规的诗,培育了丁氏百年不衰的良好家风;正是这首传之百年的家规诗,造就了丁宝桢的高尚人格。
丁公俊之子丁必荣,37岁做官,先后任四川酉阳州州判和昭化县知县,廉洁敬业。丁必荣之子丁世棻,27岁成为优贡,在贵州镇远府训导职位上,十年如一日,克勤克俭,兢兢业业。
丁宝桢是丁世棻之子,深受先辈家风涵养熏陶,无论在哪个地方为官,都留下了不朽的名声。
他在山东为官13年,先后任山东按察使、布政使,直至山东巡抚。在此期间,他做了三件名传一时的大事。一是智斩太监安德海;二是督治黄河水患;三是创办山东机器制造局。丁宝桢也被称为晚清山东最有为的官员。
在济南崇孝苑碑林里的一块石碑上,记载着同治十年(1871年)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,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。在山东菏泽黄河边的障东堤石碑上,则记载了同治十二年(1873年)黄河决口,正告假在贵州的丁宝桢赶回山东督治水患的情况。这些石碑承载了百姓对丁宝桢这位好官的深深怀念。
在丁宝桢为官十年的四川,同样留下了他良好的口碑。在这里,丁宝桢同样干了三件大事:一是改进都江堰水利设施;二是创办四川机器局;三是改良盐法。为此,朝廷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,上书四个大字:“国之宝桢。”而丁宝桢的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都江堰边上。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丁宝桢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。由于平时的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学,作为一个封疆大吏,他在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,只好上奏朝廷:“所借之银,今生难以奉还,有待来生含环以报。”光绪为之动容,称“遽闻溘逝,悼惜殊深”。礼部尚书李瑞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,把他与曾国藩、左宗棠等同推为晚清名臣之一。噩耗传出,山东父老悲恸、惋惜、哀叹,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。灵柩运至济南,士绅百姓争相“郊野祭吊”。将其遗体葬于历城(今济南)华不注山麓。山东百姓对这样一个外乡人表达了何等的挚爱与尊敬,于此可见一斑。
贤人去矣,家风绵长。丁宝桢长子丁体常,官至广东布政使;次子丁体勤,任山海关通判。其孙丁道津,曾任刑部主事,宣统元年(1909年)以道员衔在济南创设官商合办的山东泺源造纸有限公司,担任公司总经理,民国元年一度出任山东布政使。侄孙丁道衡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教育家。丁宝桢的家教家风在留给儿子的信中便可知一二:
第一,志在君民,不依阿从俗。他在给儿子丁体常的信中说:“遵率祖父家规,我之做官,志在君民,他无所问。宁可被参而罢黜,断不依阿以从俗,而自坏身心,贻羞后世也!”
联想他在山东、四川为官时采取革除陋规、清查账目等一系列扭转官风的举措,他立下为官以君民为重的家规,更让人钦佩。
第二,做人做官,要立定脚跟。丁宝桢告诫儿子:“至做官一事,原是讲求做事,其补署一切,应听之天命。万不可有心其间,一涉有心,即易入于钻营,将顺卑鄙一路,切毋以此为念。立定脚跟,做人做事,方是大丈夫所为。”
做大丈夫,不做钻营之小人,是丁宝桢自己的写照,也是对子孙的告诫。
第三,存心忠厚,多济苦救民。与对自己要求节俭一样,丁宝桢要求子孙家用不要和别人攀比,“家用务宜节省,肥浓易于致病,不如清淡之养人。华服适滋暴殄,不如布衣之适体。”同时还要存忠厚之心,多济苦救民,“事事悉存忠厚之心,不敢侮人,不敢慢人,遇有善事量力乐做,不可妄取民间一钱,如供余之内,稍有赢余,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。”
古语说,有其父必有其子,说的便是为长者一生坚守的价值追求,也就是其家风中最为鲜明的价值观,不仅融入后人的血脉,而且成为激励世人的强大精神力量,流芳泽世,砥砺人心。丁宝桢是这样,其他名人先贤也无不如此。(刘绪义)